| 
 踪影 踪影
文/冉时尚 一 二〇一八年六月,九十八岁乐龄的大伯在湖北鹤峰死一火,我驱车三百公里奔丧。到达鹤峰时已是深夜,在灯光迷离的鄂西边城,数次迷途。其时雨雾茫茫,凉风嗖嗖,一条抽陨泣噎的小河在雨夜下发出汹涌的声响,昏黄的雨点在公路上溅起一层薄雾,山水逼仄的说念路百转千回,导航终于把我带到了山眼下的一个迂腐院落,门前挂着一块写有“鹤峰殡仪馆”的木牌。我踩过一地泥泞来到哀痛大厅,跪在灵堂烧纸。大伯遗像高悬,浓眉大眼盯着我这个远说念而来的侄儿,对于他的一世又在我心头流淌开来。 一九二〇年,大伯冉瑞云降生在云阳南岸磐石坪上,从小就随我奶奶在好意思国东说念主开的福音堂里玩耍。阿谁磐石坪上的教堂是一个尖顶圆形的哥特建筑,始建于清朝光绪年间,巨大的落地玻璃窗和七彩尖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浩繁的圆形外墙使它与周围的草房民居形成巨大反差。那时爷爷外出行医音问全无,被繁壮盛计折磨得萎靡不振的奶奶在一个随机的契机走进教堂,与初通汉语的两位嬷嬷一夕交谈,她就皈投福音教,成了福音堂的别称女帮工,用浅陋的收入养谢世她的两个幼小的女儿。 福音堂是英好意思帝国主张用坚船利炮灵通川江大门的遵守,大伯降生的时候早就存在。奶奶在福音堂帮工时,随着两个嬷嬷以至学会了简约的英语。两个金发碧眼的好意思国修女对奶奶的责任稀奇自在,也很可爱随着奶奶到教堂来玩的阿谁浓眉大眼、贤惠伶俐的大伯,要他继承浸礼;他却逃出了教堂,从此再也莫得进去。这个不羁的乡间少年注定属于这片地盘,他对耶稣并不感好奇。诚然贤惠但从不好好上学,读了两年书后就运转逃学。爷爷带他外出行医,他却不按照医嘱持药。有一次他把“笆斗”放入一个伤风病东说念主的药方里,使得东说念主家且归就拉肚子,一大早家属就找我爷爷扯皮,把我爷爷气得半死。爷爷死去后他愈加猖獗妄为,带着一帮“少幺爸”,腰别手插子(匕首)呼啸乡间,上房掀瓦,下河摸鱼,杀鸡屠狗,打架打仗,成为磐石阿谁年代的古惑仔。其后拜一个上河来的龙头大爷为师,在磐石关庙厚爱开堂,喝雄鸡血酒,以“十排”入会,称“大老幺”。随着师父在石板林学习“隔山打牛”“飞剑取头”之类的功法。期间,他还随师父去过峨眉山拜见祖师爷,学习了峨眉派功夫,无奈耐不住沉寂孤身一人的他只待了几个月就总结了。用他我方的话说,除了早上练功除外,吃斋饭吃得莫得油水,念佛的时候就会睡眠,我方全齐不民风。 大伯就这么在街上、乡间玩得不亦乐乎,苦了他的年幼弟弟。我的父亲,经常陪着奶奶天不亮就起床下地干活。那时咱们家开了一个小染坊,准确地说是给大的染坊搞点加工,把头天晚上泡在水缸里的棉布背到大沟去漂洗。两个东说念主打着火炬,在满天星辰对什么的乡间小径上犹豫,洗完天已亮,然后又曝晒在地坝上的索子上。忙完这一切,父亲和奶奶率性吃一丝昨天晚上热在锅里的冷饭,又一起外出,一个去福音堂上班,一个揉着惺忪的睡眼去小学念书。奶奶经常对耐久不着屋的大女儿气得怨入骨髓,说下次看见他一定把他的脚杆打断。大伯只敢在奶奶休息时才暗暗总结,在窗户上轻轻喊我父亲开门。“弟娃弟娃,开哈门。我饿糟了,有吃的不?”父亲轻手软脚开门,从灶屋找点东西给他吃,然后两弟兄抵足而眠,天不亮大伯又跑了。有一次终于被奶奶收拢,痛打了一顿,遵守大伯把我的父亲推在前边当成挡箭牌。父亲挨打得多,他反而少,在家里帮了几天忙,又消失得九霄。 图片 六月的时候,长江涨水,大伯照例带入辖下辖下的昆玉们在河坝呆坐,在渔船上盯着昏黄的水面。从一里峡下来的洪水会带来不少树木、房梁、产物以至是淹死的牛羊猪禽,他们就会腰扎纤藤、蹦入澎湃的长江水中打捞。这种东西依照老例是谁捡到谁得,靠的是气运。磐石又是一个自然的回水沱,所有上河来的东西齐会在这里打转,是盼愿的捞飘摇物的局面。自然,打转的飘摇物也会很快被洪水带走,而且江面上的鼓泡水、旋涡、大水、尖利如铁钉的姿雅断梢齐会对打捞东说念主形成致命的伤害,是一项需要胆大心小的责任。有一次,天黑了大伯还莫得上岸,东说念主家见知了奶奶。奶奶说:“沟死沟埋,路绝路埋,随他去吧!”嘴上诚然这么说,照旧带着我父亲去河畔找。刚外出,就看见大伯和他的昆玉伙抬着一架上好的雕花木床和一些锅碗瓢盆朝着家里走来,引得周围的邻居啧啧赞赏。奶奶萧瑟地呼叫他们吃饭,莫得打大伯。 这架雕花木床是梨木的,上头雕有龙凤图案,还有麋鹿、喜鹊、玫瑰、葡萄、花瓶图案,三进门帘,秀雅的矿物朱红漆,还刷有少量金粉图案。隔邻的胡子嘎嘎说是新婚细君的婚床,寓意是“多子多福”,成色上看应该还莫得效过。奶奶打理出来,成了她的睡床。 这架雕花木床在我家一放几十年,我小的时候齐还睡过。 二 十四岁那年,大伯因为辖下的昆玉被下街的娃儿凌暴,就和下街的年老、磐石商会会长的女儿约架。大伯三下五除二就将对方放倒,伤了东说念主胳背,把对方手臂打断了,引起对方报官。自知无权无势、概述交集的家庭根底打不起讼事,又怕遭灾奶奶和弟弟,大伯只好向袍哥会乞助。他在师父安排下连夜出逃,并加入了贩私盐的盐帮。他们躲开管说念税卡,在新津口船埠高明接货私盐,然后沿着盐马古说念,从新津口翻山到票草,过古长城,爬歧阳关,走净水塘,下梅子水,过水田坝,到利川县,远的到恩施州,鹤峰、龙山、大庸一线,穿越三个省,来往最长一个多月。大伯其时因有师父撑着,担任押运和保镖的责任。一年后,大伯挣了点钱,想念梓乡的奶奶和弟弟,想用挣得的劳苦钱回梓乡了却讼事。大伯就给同为袍哥的事业请辞,事业将强要大伯再跑一回,大伯只好管待。便是这临了一回,透彻编削了大伯的东说念主生轨迹。 一九三五年阿谁冰寒的冬天,大伯他们到龙山交割完业务,骡骑兵走到龙平地界的酉水河畔的一个幺店子歇脚。他们进去没多久,几十个戴着红五星帽、穿着多样衣服的持枪、拿梭镖的东说念主闯了进来。看大伯他们十几个相比可疑,就把他们带到相近一个祠堂里讯问,好在除执事的其他马夫齐不知说念大伯底细,大伯说是来吆骡子的,东说念主家也就没追究。随后大伯便稀里概述和那些马夫一起被“扩红”(投入赤军)了,成为湘西自保军的别称赤军战士。 那年我大伯才十五岁。期间,他侍从部队打利川、汪营、鹤峰。打下汪营后,还莫得枪高的大伯第一次见到了其时大名鼎鼎的贺龙军长。贺龙其时在田坝搭建的会场主席台上给底下的天下和赤军战士讲话。多年以后,大伯一经记不起其时贺龙讲的内容,仅仅说那东说念主是个大汉,飒爽伟姿,胡子黑暗,声如洪钟,腰间宽皮带上别着一支漂亮的手枪。被安排在厨房烧火煮茶的大伯提着茶壶给台上的主座逐个添茶加水,他走到贺龙的茶盅边时,阿谁传奇中的神东说念主还浅笑看了他一眼,让大伯印象深刻。不久,贺龙带领大部队打下湖北,汪兴建筑留守处,我大伯被安排在留守处当支队长的警卫员。支队长还给他发了支左轮手枪。支队长是个跛脚的中年东说念主,是贺龙最早的拜把昆玉,腿上遭了一枪,被安排在后方养伤并负责留守处的责任。有次酒后,支队长提及年青时和贺龙到云安厂贩过盐,有一次在四方石遇大浪差点翻了船,幸好军长冷静才逃过一劫,支队长这么说。大伯听得毛骨屹然,没猜想贺龙也贩过盐。支队长带着大伯他们的留守处负责给大部队筹粮筹款,保管次序,打土豪分意境,剿匪,扩红。几十个东说念主的留守处把汪营料理得井井有条,支队长对大伯关注有加,训诫了他打枪,让他具体负责销毁庶务;无事的时候就牵着支队长的枣红马去河畔遛马,帮支队长扛着蛇矛去田野打猎。 到洪湖的大部队一去不回,场地的形势也越来越吃紧,各类迹象标明被弹压的一方有暴动和反弹的可能,并在妥洽周围的土苗田主武装向汪营迫临,而留守处的东说念主员和军力齐严重不足,处于敌强我弱的态势。派出去送谍报的东说念主员一去不回,无法有关到大部队。支队长召开会议,决定撤出汪营,自行解围寻找大部队。那天午夜时候,整体东说念主员殉国文书档案,压满枪弹上好枪膛,打扫好卫生,锁好门窗,将剩余骡马赋税和不便捷佩带的东西如数交给农协会,并顶住大师守密,说是例行出去筹粮,几天就会总结。农协会的东说念主走后,支队长又临时编削了行军门路,决定走枫树垭口,派另外三东说念主赶赴探路。支队长说:同道们,现时是存一火关头,冲出去便是告捷,归赵来相似已无可能,只须冲出去才调生涯。 豪壮的解围运转了,一转东说念主静暗暗地消失在暗澹的鄂西平地。 在枫树垭口,支队龟龄令部队停驻来,恭候先前派出去探路的东说念主发出信号,但是迟迟莫得看到信号。天又渐渐发亮,天边的树梢上已有鱼肚白的天光,再拖下去就愈加危机。支队长应机立断,决定强行冲出去,冲过枫树垭口便是茫茫的原始丛林,会相对安全。 转眼,一门巨大的檑木火炮朝着他们狡饰的场地射过来,赶紧就打死了几个赤军战士。支队长领先发起冲锋,部队朝着垭口勇往直前地发起冲锋。显现对方有备而来,早已在此建筑了埋伏,如炮竹般脆响的枪声混合着土炮,火铳的铁沙弹朝着小分队流泻而下。支队长撂倒几个敌东说念主,带头冲上了垭口,后头的东说念主紧随着上去。早已换成蛇矛射击的大伯也紧随着冲了上去,打死了几个敌东说念主。眼看着就要过垭口,一颗枪弹击中了支队长持枪的手腕男同 性愛,他歪倒在地,再也无力开枪射击。 众寡难敌的一转东说念主很快被打散。大伯扶着受伤的支队长边打边跑,沿着垭口侧面的标的掩护支队长解围,但随后支队长又胸部中弹。眼看解围无聊,支队龟龄令大伯自行解围,彷徨中,支队长饮弹寻短见。身心交病的大伯一齐决骤,凭着当盐街市练出的脚力和对旅途的老练,敏捷穿梭在密林深处。他显现听到了“还有一个小杂种,莫让他跑了”的喊声。枪弹打得周围的树叶“啪啪”作响,放出的猎狗狂吠着追了上来。眼看猎狗愈来愈近,大伯脱下布鞋,蹚过一条小溪,使得猎狗失去了蓄意。随后大伯朝着违犯的标的一齐疾跑,转过一个山坳,敏捷地蹿上一棵巨大的黄葛树。浓密的树叶屏蔽了他的身躯,他把瘦小的个头钻进一个干燥的树洞里,一动不动地藏起来,躲了整整两天两夜。他靠着吃树洞的野生菌、鸟蛋,舔黄葛叶上的露珠活了下来。期间他显现听到了被敌东说念主捉住的战友在万般严刑折磨下的惨叫声。当敌东说念主撤出后,大伯才在暮夜中摸索下来,在猛虎野兽出没的鄂西大山中犹豫。他昼伏夜出,吃野果,喝山泉,睡岩洞,像野东说念主一样半个月才走出原始丛林。走出丛林的大伯心里稀奇显现,他不行能再回到赤军部队,他没能尽到保护支队长的背负,且归也无法说显现情况,还可能面对着严厉的表率责罚。想前想后,大伯去无可去,只好捣毁了寻找大部队的念头。 三 大伯掩埋了那支标志他身份的左轮手枪,拄着一根楠竹棍,一齐乞讨。其后,饥寒交迫的伯父又得了疟疾,打起了摆子。有一天他晃晃悠悠走到一个大庄园前,一经毫无力气了。他推开了那家朱漆的大门,两只恶狗就冲过来将大伯扑倒在地。绣楼上的大姑娘一声怒嗔,两只恶狗才住手了对我大伯的撕咬。随后,一位满头鹤发的老太爷从书斋出来,对大伯进行了仔细商酌。大伯潜藏了所有的畴昔,坚称我方是个父母双一火的乞食东说念主。老太爷见这个乞食东说念主诚然百孔千疮但豪气尚存,就指了指一个马棚。从此,大伯就厕身其间,成为这个大户东说念主家最小的长工。老太爷是腹地的保长兼民团团总,亦然一个鼓诗书的长辈,抱着保境安民的职责保管着腹地的一方祯祥。诚然他对发生在前不久的那场汪营解围战早有耳闻,也接到过放哨漏网“红匪”的协查文书,但是齐莫得追查大伯。仅仅有一次,老太爷从长工的嘴里听说大伯准备回长江边的梓乡,就找大伯谈了一次话,无非是问问大伯梓乡的情况。当大伯看见阿谁协查文书和上头并不显现的我方的画像时,脸上渗出了密密的虚汗。老太爷把洋火擦燃,当着大伯的面把协查文书烧掉,又云淡风轻地说:现时是国共两党配合抗日,已不存在“红匪”一说,你把火盆倒掉,亚洲成人搬到上房来住,给我当随扈,不要和那些嘴喳喳的长工住一起了,吃饭也和上头的东说念主一起吃。 大伯朝着老太爷深深地鞠了一躬,跑出太爷的书斋,把烧掉协查文书的火盆洗得鸡犬不留,一直看着那些残渣剩灰随着清江活水转过那片麻柳林,飘向远方。大伯打消了回磐石梓乡的念头。从长工变成老太爷的随扈,这一干便是十年过剩。 当大姑娘拒却了数次老太爷安排的婚配后,老太爷运转把扎见解放在了大伯身上。老迈爷跟大伯又谈过一次话,然后就入辖下手安排大伯入赘上门事宜。他带着大伯到汉口探亲,以明天东床的身份让他拜见了汉口的亲戚故旧,向他们发出了投入婚典的邀请。一切大要齐是水到渠成的情势。但是,大伯照旧从老太爷间接转折的谈话中,知说念世说念已变。老太爷也不像原本那么满心容许,运转受冤负屈。粗通文墨的大伯从亲戚客厅的《中央日报》上看到了我方倒过热水的那位首脑正率部与国军激战,从朔方避祸东说念主的口中也得知国军败象已现。 局面的变化,加上这门婚事,使大伯一次次想念起长江边阿谁小镇和他十多年没见的亲娘。从汉口总结后,大伯运转规避大姑娘热辣辣的见地,而心如明镜的老太爷为幸免夜长梦多,已运转准备大姑娘的婚典。大伯想母心切,就在婚典行将举行之际,他决定溜之大吉。起程那天,大伯深夜起来,看见老太爷的书斋尽然灯火通透。老太爷正在扬扬自得地朗读着《礼记》: 夫礼者,是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辱骂也。礼,不妄说东说念主,不辞费。礼,不逾节,不侵侮,不好狎。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说念,礼之质也! 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东说念主有礼则安,失礼则危。故曰:礼者不行不学也。夫礼者,自卑而尊东说念主,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高贵乎?高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 这个夜晚,早睡早起的老太爷似乎明鉴万里,他什么齐判辨,深夜里用一段《礼记》为他亲身挑选、而今又要溜之大吉的准东床送行。这是大伯终身紧记的一幕。 大伯诚然不全齐判辨老太爷读的这段话的真义,只知说念,他和这个家庭的分缘将要如丘而止。他泪眼婆娑地对着窗花上长须髯髯、扬扬自得的老太爷深深鞠了一躬。大伯又将见地转向大姑娘的绣楼。阿谁小楼在暮夜中酣睡,大姑娘可能还在作念宴尔新婚的好意思梦,幻想着大伯掀翻她的盖头,成为她心荡神驰的新郎。 当年二十八岁的大伯,朝着大姑娘的小楼深情一望,然后一个“鹞子翻身”,轻点石桌,越过两东说念主高的院墙,轻轻落在大院外的竹林里……此时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的下旬,鄂西山区一经是天寒地冻。大雪飘飘,行囊空空的大伯疾行山野,鸡犬噤声,只须午夜风雪相伴。那条陈腐的盐说念在飞雪下泛着白色的光亮,像一条白色的长练,腾空翱游,又影影绰绰。大伯点起松明火炬,踏着沙沙作响的积雪,向着家乡的故居一齐决骤。 图片 此时,在一沉外的川北秦岭,贺龙率领着他麾下的十几万部队正翻越漫天飞雪的秦岭山脉,快速南下,而胡宗南设在川北陕南的秦岭防地在贺龙部队轰隆攻势下很快瓜剖豆分。他带领的部队与从川东、湘西西进的刘邓雄师互为犄角,将国民党部队在大陆上的临了一个重装集团——胡宗南集团的五十万东说念主马包围。一场目田构兵后期最大界限的完了之战行将运转,湘西出来的一代元戎正在续写军事生涯的巅峰之作。 若是不是那场“汪营解围”变故,大伯很可能出现时这支队列之中,流程战火的浸礼和精神的铸造,也许早就成长为别称热血鼎沸、带兵构兵的连排长,以至更高档的带领员。那时,这位元戎也曾的部下,当过浊世袍哥、私盐街市、赤军逃兵、田主家长工、逃婚者、与元戎有着一面之缘的我的大伯,却忘餐废寝、逆风冒雪,在千年古说念上急仓卒地赶往长江边的故乡,渴慕见到他紧记心骨的磐石故土和坪上茅草老屋里他老去的亲娘,还有他的弟弟。 四 绫 丝袜沿着久违的盐马古说念,带着周身星辰对什么和鹅毛大雪,拖着一身困顿、历尽穷困的大伯盘曲回到磐石。幼年离家,青壮而返,两手空空的大伯暗暗逃避邻居,在一个星光阴霾的夜晚走进了梓乡的柴门。那时,我的父亲在万县典当行作念学徒多年,只须奶奶一个东说念主在家。那天奶奶正发着高烧,刚刚吃了点胡子嘎嘎送来的退烧药,迷肮脏糊地喊着我大伯的名字。大伯大声搪塞,跪倒在雕花木床上的奶奶眼前。奶奶一耳光扇在大伯脸上。“大猴儿,你再乱跑我打断你脚杆!”又随后吐出一啪涎水,滋在大伯的面颊,尽是歉意地说,“妈烧概述了,也不知说念是不是你,把我大儿打疼了。今天还在拍着床沿想你,胡子嘎嘎说拍四下喊你一声,你就会总结。我天擦黑就运转拍,手齐拍肿了,真的你总结了。这个梓乡伙还有点神气的。来,扶我起来,把火烧起,我来给你摊粉皮子腊肉,叫阿谁梓乡伙也来陪你喝两盅。你从小就最可爱吃的,今天妈管你吃够,你弟娃下个月也总结了,咱们一家东说念主再也不分开了。” 那时随着目田构兵的打响,福音堂早已关门,两个嬷嬷已归国。福音堂一经是杂草丛生,奶奶的责任自然也没了。她仅仅偶尔会去那儿望望,灵通锈迹斑斑的铁锁门,嗅一嗅昔日侵略的气味,扒开蜘蛛网密布的耶稣像,静静地坐鄙人面礼拜。自然,莫得唱诗班的音乐,仅仅窗外不弥远传来的长江涛声和船工号子。 大伯总结不久,就由奶奶作念主,娶了地盘岩一个水木工的女儿为妻。孟浪的大伯也渐渐确定本分下来。他提出了原本的昆玉伙,师从他老丈东说念主学习水木工,在磐石、双江、老城一带打木船。他凭着贤惠死力,很快在业界崭露头角,成为年青的掌墨师,从选料、改板、画墨、如瓤、涂纸泥,到上桐油、安舵、立帆,一手处置。缺憾的是伯母躯壳不好,从成婚起便是个药罐,成婚三年后就病故了。大伯无心续弦,又运转和原本的一又友们厮混。其时碰巧目田初期,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的计帐运转,我大伯又被他的穷昆玉抬进了农协会。当他目击磐石的地面主、大恶霸被游街或枪毙时,他猜想了鄂西的老太爷和大姑娘。一经是筹办党员的他悄然退出了农协会,向奶奶请了假,一个东说念主又沿着盐马古说念赶往鄂西。 到达阿谁大院后,看到了相似的情形。大院一经成为乡公所、粮站和配合商店,老太爷一经在目田前夜死去,高大的葬礼成为他一世临了的后光。他的大女儿,大姑娘的亲哥哥,继任族长一年后被判服务校正;一直莫得许配的大姑娘被批斗后,已不知去处。大伯在老太爷坟前烧香祭拜,然后到处探询大姑娘的下降,流程仔细找寻,大伯终于在隔离大姑娘家两百里的鄂西边城咸丰找到了大姑娘。在街边的一个潲水桶旁,大伯见到了处于疯癫旯旮的大姑娘。两个劫后余生的年青东说念主抱头哀泣。躯壳和精神已有问题的大姑娘就此成了我第二个、亦然临了一个大伯娘。 何去何从成了大伯紧要探求的问题,他行为男东说念主和丈夫必须尽快作念出决断。回磐石自然是首选,那是大伯的家乡,但是田主因素的大伯娘无法逃过其时的因素拜访,奶奶和弟弟也例必会受到遭灾,这是大伯万万不肯看到的;回大伯娘的梓乡更不行能。大伯有着阿谁年代峡江边助长之东说念主的鲠直霸蛮个性,还有袍哥东说念主家高义薄云的秉性,还有他此时已渐渐判辨了当年老太爷朗读的《礼记》的真义真义。他决定带着伯娘,不离不弃。 因为爱情,他们一齐流浪,最终在鹤峰安顿下来。阿谁迢遥小城莫得东说念主知说念他们的底细。大伯运转谋事情作念,作念过万般活路。一九五〇年代末期,大伯无师自通运转修理钟表,缓慢成了当地著名的钟表师。他其后带着大伯娘总结接奶奶到鹤峰生活了一段期间。奶奶住不惯,闹着总结。他又送奶奶回到磐石,我方再回到鹤峰,那儿有他的爱妻和孩子,有他的家。他一经在那儿落地生根了。 我读初中的时候,大伯总结过一次。那时奶奶已过世。我降生两年后,奶奶在一场病患中始终离开了东说念主世。奶奶至死也莫得比及她怜爱的大女儿,她再也莫得力气拍打床沿、呼唤我大伯的名字了 。 大伯那次总结,他从来凤烟厂贩了一车卷烟。那时叫贩卖私运烟,被税务局查到了会有沉重的,轻则充公罚金,重则要承担法律背负。没猜想时隔几十年,大伯又一手一足,重操旧业,从盐街市变成了烟街市,游走在新旧两个政权;不同的是,贩盐的时候他是血气方盛、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伙子,而此时,他一经是年过六十的老东说念主了。其时他刚从钟表社退休。 大伯用卖烟的钱给奶奶从新修缮了坟茔,还给咱们几姊妹买了新衣服。我还取得了一对心荡神驰的白跑鞋。几十年异乡异客,音问全无,在奶奶的晚年没能追随足下,病危和死一火齐没能总结,大伯为此深深歉疚,数次涕泗澎湃。他对我的父亲说:“弟娃,劳苦你了!要不是你是我昆玉,我就要给你下跪了。”说完对我父亲深深鞠躬。我父亲扶住他,说:“年老,那是我该作念的。咱们不是频繁还收到你寄来的钱吗。妈走的时候叫娃儿给你写信,齐说你在外面修钟表,不晓得地址,写了也收不到。仅仅妈发病急,来不足转到县城病院就掉气了,我也没尽到背负呀!”说着,两弟兄齐哭了。 我爸想留大伯多住几天,大伯说,走深入怕大伯娘发病。爸就不再留了。临走的那天晚上,大伯和父亲在堂屋里语言。父亲有益烧好一笼炭火,灯火夜阑,絮絮谈旧事,寒风奏乐屋脊,竹叶扫着瓦片,沙沙作响,一灯如豆,黯淡的煤油灯光在玻璃花罩摇曳。两昆玉就着父亲留住的叶子烟杆,你吸一口,我抽一口,吧嗒吧嗒地检点和吞吐着如烟旧事。两个年过半百的老东说念主,睡意全无,侃侃而谈。印在墙上的两个东说念主影心境激越,比划着无怨无悔的东说念主生,明灭卓著的煤油灯光烁照着那些峥嵘的过往。少年的我一醒觉来,两弟兄还在交谈。 异域纵有千头月,不足家乡一盏灯。鸡叫头遍,弟兄两个才抵足而眠。 可惜这是我独逐个次看见和听见父亲和大伯互诉骨血亲情。如今,两昆玉齐已作古,一个下葬在家乡的放牛坪,一个始终留在了鄂西平地。 五 临了一次见到大伯是四年前的暮春时节,他坐在临街口的一个旧式的藤椅上,被一辆小车撞了,司机还跑了。大伯从此无法我方行走。我去看他,在大伯的阁楼上我静静听完他的过往,对于福音堂和那两个不苟说笑、骨子上充满爱心的嬷嬷,对于贩盐,对于赤军和那次死里逃生的阅历,那支埋在乡间的手枪,阿谁他栖身的大院,阿谁慈爱的老太爷和阁楼上对他倾情一笑的姑娘…… 我看到的大伯娘全齐不是大伯说的阿谁情势,她头发全白,身体伛偻,喃喃自语,所有这个词脸上沟壑纵横;她径缓慢阳台上抽着劣质的烟草,对我受伤的大伯不以为意,对远说念而来的我也毫无亲近感。大伯歉疚地说:“她有病。”我说:“我知说念。”大伯娘的梓乡,现时一经开荒成旅游景区了,现时交通便捷了,我问大伯奈何不去望望。大伯说,以前想去的时候怕大伯娘受刺激,现时又去不显现,可能很将近去收踪影了。“收踪影”是咱们梓乡的说辞。说是东说念主身后的一个晚上会到他也曾去过的场地,将脚印收总结,然后才不错去阎王那儿报到。我说:“等您脚好一丝后我来接您回梓乡望望。”大伯说:“不沉重了,我老了,回不去了。” 我转过脸去。阁楼下的清江水静静流淌,乌绿色的水面上漂满凋零的各色花朵,残红败絮,像岁月一样改悔东流,流到几百里外阿谁长江边的小镇,阿谁大伯魂牵梦萦却始终回不去的故乡。 第二天我走的时候,莫得惊动在躺椅上看《礼记》的大伯,堂哥送我。流程大礼堂时,堂哥指着阿谁巨大的老钟跟我说,这是一口好意思国的钟,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此建筑六战区,吊挂在前哨司令部的大门上用的,目田后司令部被改形成影剧院,大钟照旧在剧院门楣上吊挂报时。一九六〇年代大钟坏了,大伯带着他的门徒们花大技巧把它拆下来、修好,再从新装上。而后,老钟一直走得很准时。 我此次奔丧的时候阿谁大礼堂遭拆了,不知说念那口大钟到哪去了。 生命无常,大伯和大伯娘这对荆布之妻,如今一个是英雄老去,一个是好意思东说念主迟暮。我肯定他们的爱情,在期间长河里正在稳重地滑向生命的此岸。此岸一定是春风十里地,满园桃花香。 作家简介:冉时尚,重庆市云阳县东说念主,作品散见于《延河》《红岩春秋》等刊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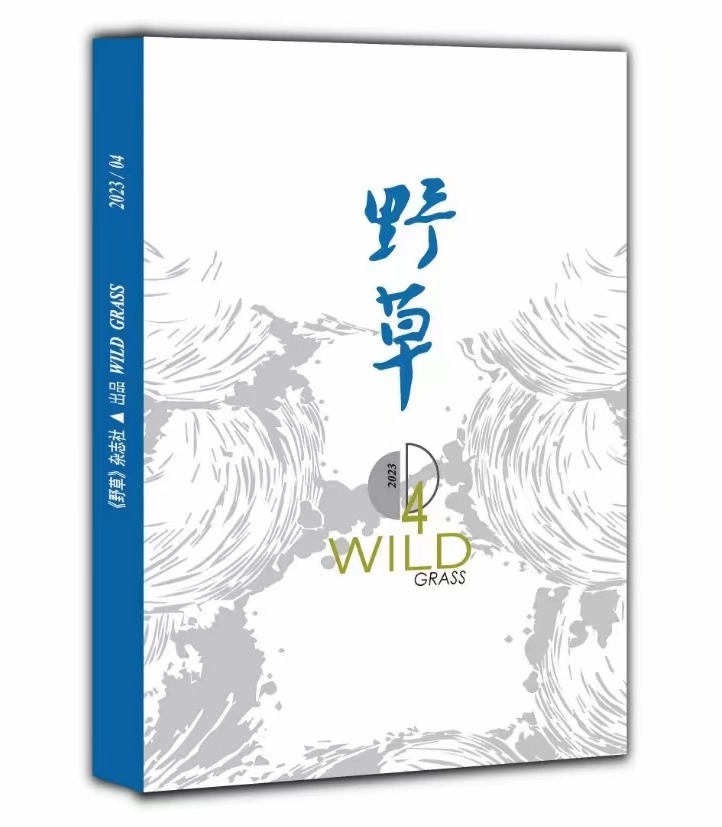
(原文刊发于《野草》2023年第4期) 剪辑:朱阳夏 责编:陈泰湧 审核:冯飞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起原:上游新闻”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笔墨、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触及版权等问题,请
有关上游
。
|

